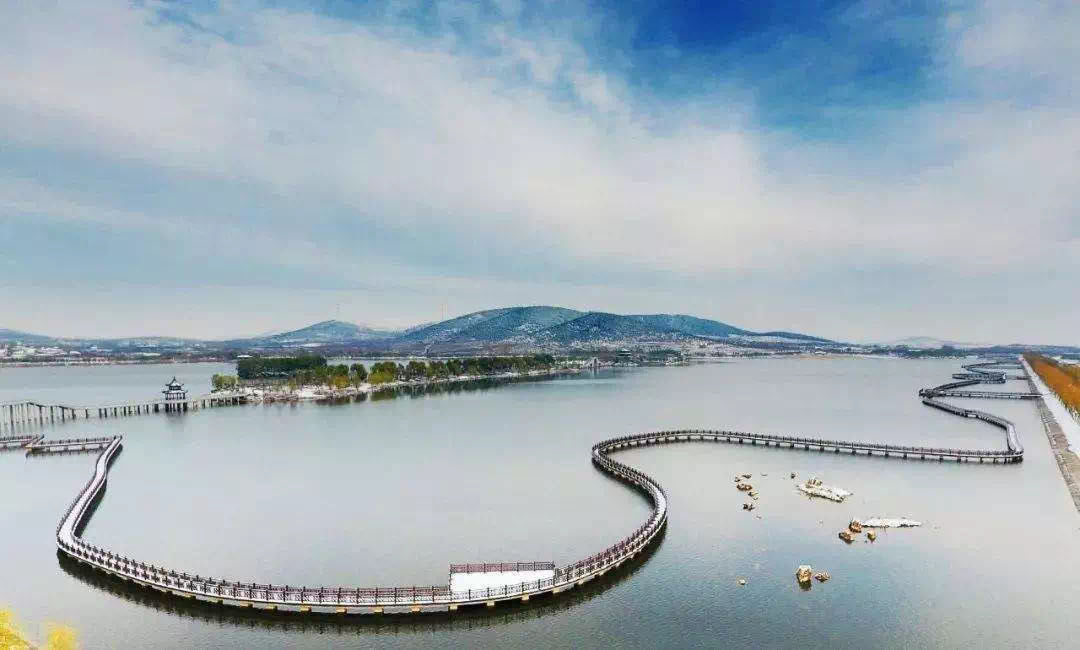周淑娟 何圭襄 著
2020年1月第1版
南京出版?zhèn)髅郊瘓F 南京出版社
“深入生活����,扎根人民”是黨中央對文藝工作者的殷殷希望和諄諄要求。在徐州����,這已經(jīng)變成了作家、文藝家的自覺行動——從“小我”走向“大田”�����,走出了作家的新足跡����、新視野,更走出了作品的新高度�����、新境界���。
徐州市作協(xié)副主席���、散文作家周淑娟的采風和創(chuàng)作實踐表明����,火熱的時代�、多元的社會、偉大的人民�����,才是文學藝術(shù)的根基所在�����、根源所在�����。長篇報告文學《賈汪真旺》以宏闊的視界���、細膩的筆觸,描繪了新時代背景下賈汪波瀾壯闊的改革發(fā)展畫卷和普通百姓的人生際遇����,故事百轉(zhuǎn)千回、人物栩栩如生。是近年來徐州���、江蘇乃至全國報告文學創(chuàng)作的新探索�、新收獲�。作品大氣磅礴,而又清新婉麗���,既有深厚的哲學思辯���,又有獨特的文學鋪陳。甫一問世���,即獲得文學同仁和社會各界的關(guān)注與稱許�����。
近日����,一級作家��、徐州報業(yè)傳媒集團總編輯王建以九問的形式���,與周淑娟展開訪談�����,交流創(chuàng)作心得與文學感悟��,以期對更多的寫作者和讀者有所啟迪��。
Q1.你是一位大家熟知的散文作家�,此前一致專注于自己的創(chuàng)作半徑,收獲頗豐���。是什么樣的緣分人物或事件促成來寫賈汪的報告文學的?
我對《紅樓夢》有種無法釋懷的熱愛��,文友也評論說《紅樓夢》是我寫作的興奮點��,我甚至認為我對散文這種文體的運用都來自它——因為喜歡《紅樓夢》這部小說而以散文的形式表達自己和自己的發(fā)現(xiàn)——不吐不快����,一吐為快。我曾說過自己是“十年一覺紅樓夢”�����,其實這個夢已經(jīng)做了很久。2018年6月�����,我的散文集《縱橫紅樓》獲得第八屆冰心散文獎�����,再次證明這是一個很美的夢�����。
一切跟著愛好走的人生���,有時是苦惱的����,更多的時候是滿足的����。這種滿足,大多滿足的是自己��,無法顧及別人那些世俗需求��。我沒時間糾纏于這到底算是任性還是“一癡”。不管是任性還是率性���,成功還是失敗���,英雄還是狗熊,過去的都過去了���,該留下痕跡的也都留下了��,現(xiàn)在還要為未來去沉淀�,每一天都是新的開始�����,我沒有任何遺憾�����。“唯有對愛好�,年齡才不是限制�����,反而是成全。”每當阻力和壓力結(jié)伴到來時��,這句話就從我心底迸發(fā)出來���。
從愛情唯一到青春唯美���,從人情冷暖到人性善惡,這是之前我讀《紅樓夢》的心理歷程�。如今,生命觀照和哲學關(guān)注促使我轉(zhuǎn)向——轉(zhuǎn)向現(xiàn)實��,走進生活��。
Q2.以前對賈汪的印象��,如果用一個字或一個詞來表達�����,是什么�����?為什么是這樣的���?
對賈汪的印象���,可以用“不確定”來表達�����。因為工作關(guān)系��,我曾多次到賈汪區(qū)去���,但我一直無法捕捉它的氣質(zhì),甚至總覺得它很遙遠���,雖然從家里到那里和我從家里到單位的路程差不多���。所以,內(nèi)心深處我或許對它有種好奇�。
Q3.你工作很忙����,寫作很累。大量的實地采訪是怎么完成的��?一共采訪了多少人?他們的名單是如何確定的�?他們是不是充分地完整地表達了自己的訴求?如果是���,也這樣在你的作品里面體現(xiàn)了嗎����?
特別感謝您提到我的忙和累�����,確實如此�。一個周六又一個周六,一個周日又一個周日�����,從秋天到冬天����,從冬天到春天,從春天到夏天��,從炎炎盛夏又到秋冬季節(jié)。
為什么都是周六周日����?寫作在一些人眼里、嘴里是一種罪�。我是有工作的人,又是高度自制自律的人�����,就給自己定下“規(guī)矩”:所有的采風都要在業(yè)余時間完成����。我可以驕傲地說,我沒為《賈汪真旺》這本報告文學請過一天假���,我的本職工作也做得很好���。這種驕傲很可笑,是不是��?但它是現(xiàn)實�,是生存。
采寫到底是個什么情形��?恰如我先生在后記所寫的那樣:現(xiàn)在����,當這部作品擺在案頭的時候,我不禁想起了我們一年間的種種合作細節(jié)��。所謂的合作�����,是多種形式的��。比如�����,一次次去賈汪采訪��,就是我在開車����,她在副駕位置坐著。一次次的訪談����,常常是我來發(fā)問,她來記錄。我以新聞的眼光打量和思考�����,她以文學的手法表達和呈現(xiàn)�����。每一章����、每一篇、每一段����,或由她開頭,或由我開篇����。我寫成后,由她來刪減騰挪����,或她寫成后由我來騰挪刪減。標題����、正文���,打磨���、潤色�,大規(guī)模地“砍”���、小范圍地“敲”����,如此一而再�����、再而三����,終于完成了這本書的創(chuàng)作。
行走中�,采風時,我們認識了不少人����,聽到了不少事���。最初受訪的人,有些是從新聞中發(fā)現(xiàn)����,有些是當?shù)匦麄鞑块T推薦的,有些是我們主動搭訕���。在此基礎上���,我們采用發(fā)散性采訪法,就是通過一個人認識一群人���,通過一件事找到好幾個同類事件����。于是���,一發(fā)而不可收�����。
借此機會���,我要特別感謝賈汪人給予的支持和幫助�。因為我們的采風都在周末和節(jié)假日完成����,他們便犧牲了自己的時間來配合我們�。他們,是幾十個��、上百個賈汪人的統(tǒng)稱��。無需霧里看花�,也不必水中撈月,他們坦誠而友好���,振奮了我那潛沉良久的精神�,治愈了我那美好深處的憂傷���。生命因理解而延長�����,生活因懂得而豐富�����。
李燕�、李路、張濤�����、吳連營���、孟慶喜�����、王秀英����、解玉初��、趙孝春……或為我們提供采訪線索���,或接受我們的采訪�,不管是耄耋老人還是職場中人,他們的身上�,都讓我感受到了一種精神,一股力量�����,那就是光明�����、善良����、美好�,勤勞、執(zhí)著�����、努力���。每次回望賈汪的人物和風物�����,分明有無垠的希望給予身心力量����;每次站在賈汪這片土地上,都能看到嶄新的生機破土而出��。
更為重要的是����,我們逐漸意識到,賈汪在資源型城市轉(zhuǎn)型發(fā)展��、采煤塌陷地生態(tài)修復�����、農(nóng)民口袋腦袋雙雙富裕����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“雙山理論”方面的探索經(jīng)驗和成果,對全國各地應具有啟迪借鑒價值�。
我個人認為,我沒能充分地完整地表達出他們的訴求�,作家的能力有限,作品的體量也有限。
Q4.我看了你的書���,記住了一些人的故事�����,也更立體地認識了賈汪����。賈汪的“旺”果然有它的內(nèi)在邏輯��。但總感覺�����,還有一些話���,藏在你這部作品的字里行間。如果是這樣�,那是他們沒說,還是你沒寫���?
您很敏銳�����,為此我心懷感激����。記得有個老師曾經(jīng)說過,報告文學作家可以在文中埋下“地雷”�����。我沒有埋雷���,但是我在字里行間留下了煙火爆竹�,留下了帶刺玫瑰——有胸懷的可以發(fā)現(xiàn)真善美�����。有些文字已經(jīng)寫好�,但因為種種原因忍痛刪除了一部分,又因為種種考慮痛下決心刪除了一部分���。
Q5.從文體識別上來說���,散文和報告文學是近親��。非虛構(gòu)�,是它們共同的標簽����。你的這個作品,也可以說是散文體的報告文學����,或者說是報告文學體的散文。當然�,這不重要。我想問的是����,游刃于兩者之間,寫作的痛苦和快樂是怎么分割的���?
您對文體的識別�����,我認可。我是第一作者�����,第二作者何圭襄是我先生。我們巧用業(yè)余時間�,以“報告”和“文學”的疊加優(yōu)勢,力圖勾勒“賈汪真旺”的現(xiàn)實圖景和時代軌跡�����,剖析“賈汪真旺”的動力之源���、文化之源����、精神之源�����,并揭示出“賈汪真旺”的精神力量及其生發(fā)機制�。
正如您所說,游刃于兩者之間���,有痛苦有快樂�。先生以他一貫的謙遜內(nèi)斂在后記中寫下這么一段話�,可算是給出部分答案:再密切的合作也會有爭執(zhí)���。比如說,她改寫我的東西�,總是把她認為多余“的地得”和“了”字刪掉。這種“粗暴”的做法常常引來我的抗議——我就要這樣表達��,這就是我的風格�����。但是���,真正遇到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�,我總是謙遜地表示接受����。因為我也知道,報告文學它不僅僅是報告����,更是文學。報告修飾了文學�,文學才是結(jié)果,在文學的修養(yǎng)方面����,她自是高我一籌,我必須服從����。
他還用極為詩意的語言評價:一本書,簡直就是積字成雨——今夏的雨����,磅礴傾瀉,成汪洋����。
一年里,忙�,累,苦����,是常態(tài)。忙到什么地步�����?忙到“不能容針”����,這是《紅樓夢》評點中的一句話����。即使這樣��,我仍會唱“讓我們敲希望的鐘��,讓我們推希望的門”����。是的,鐘不敲不響���,門不推不開��。有誰知道�,在進行《賈汪真旺》采訪創(chuàng)作的同時����,我的另一本散文集《愛比受多了一顆心》也已經(jīng)付梓,即將與全國讀者見面��。
當然,也有收獲的喜悅�����。沒有一年的忙和累��,就不會有對賈汪的深挖掘和再認識�,也不會有對賈汪真旺的文學觀察和文字呈現(xiàn)�,更不會有對賈汪的持續(xù)關(guān)注和無窮熱情。
Q6.當下的報告文學創(chuàng)作有一個通病����,就是既沒有真實的報告,也談不上手法上的文學�。散文創(chuàng)作的經(jīng)驗遷移,在這部作品里的表現(xiàn)你滿意嗎�����?或者說�,這部報告文學的創(chuàng)作對你未來的散文寫作有新的啟迪嗎?
散文創(chuàng)作的經(jīng)驗遷移��,我很滿意����,但我更在意讀者滿意不滿意��。我等著讀者的反饋���。這部報告文學的創(chuàng)作對我未來散文的寫作一定會有影響,具體是什么我還無法清晰地說出來�,但我感覺到一扇門已經(jīng)打開,我看到了文體遷移或者說是文體突破的光�����。也許����,文體并不重要,重要的能夠表達一個作家的真知真見�����。
Q7.“表達自己的發(fā)現(xiàn)”是作家和作品最個性的本質(zhì)屬性�。但是,這個“自己的”和“發(fā)現(xiàn)”你是如何看待的���?
每個作家表達的都是自己的發(fā)現(xiàn)��,但怎樣表達自己和自己的發(fā)現(xiàn)值得深思�����。在浮躁的當下���,我告訴自己�,文學是自己的文學���,發(fā)現(xiàn)是自己的發(fā)現(xiàn),但只有“自己”無限曠達�、無限遼闊,才會有相對應的“發(fā)現(xiàn)”���。此生�����,我會為此不懈努力���,不停思考。
Q8.時代和社會���,是一個作家躲不開的背景����,也注定了一個作家的文學坐標。一個作家如何在生活的“大田”里獲取營養(yǎng)���?
比如說我的《紅樓夢》系列隨筆���,寫的就是《紅樓夢》的生活和生活中的《紅樓夢》,說到底����,也就是我的生活體驗和我對《紅樓夢》的認知。沒有一定的生活閱歷和藝術(shù)素養(yǎng)�����,我不可能讀懂《紅樓夢》��,而對人情人性的了解����,是讀懂《紅樓夢》的最基本要求。寫作報告文學���,更是和生活面對面��,手拉手�����。我可以肯定地說���,生活會給你驚喜����,給你養(yǎng)分���,千萬不要懷疑這點。
Q9.彼得·阿克羅伊德的《倫敦傳》我很喜歡����,也希望看到我們這個時代的《賈汪傳》《徐州傳》。下一步�����,還有創(chuàng)作報告文學的打算嗎��?如果有人寫賈汪傳,你會給些什么建議呢�����?
《倫敦傳》是一部呈現(xiàn)倫敦上下兩千年的史書�����,從正史寫到民間傳說���,從飲食寫到消遣娛樂�����,它的作者彼得·阿克羅伊德����,是英國有名的傳記作家��。
我聽說過這本書��,但還沒讀到�����。謝謝您推薦,我馬上就會去買這本書�,然后讓這本書伴隨我度過這個春天。我是寫作者�����,更是閱讀者——我對閱讀的興趣遠遠超過寫作�����。除了文學�����,我對歷史也保持著不衰的興趣——所有過往�����,曾經(jīng)都是活潑潑的���。
寫作中,“史”的概念���,我一直持有����。我知道,只有“史”與“文”結(jié)合��,才有“力”與“度”的糅合��。
下一步會寫什么�,很難說,我很少規(guī)劃什么�����,多看時間和機緣����。不過,我確信我會持續(xù)關(guān)注賈汪�����,就如同我對《紅樓夢》——從來不需要想起�,也永遠不會忘記。走出賈府走進賈汪�,走出紅樓登上青山,這是一段人生����,反向而行�����,又何嘗不是一段人生��!
如果有作家寫《賈汪傳》�,希望他首先是一位賈汪人��,正如我希望《徐州傳》由一位徐州人來書寫���。